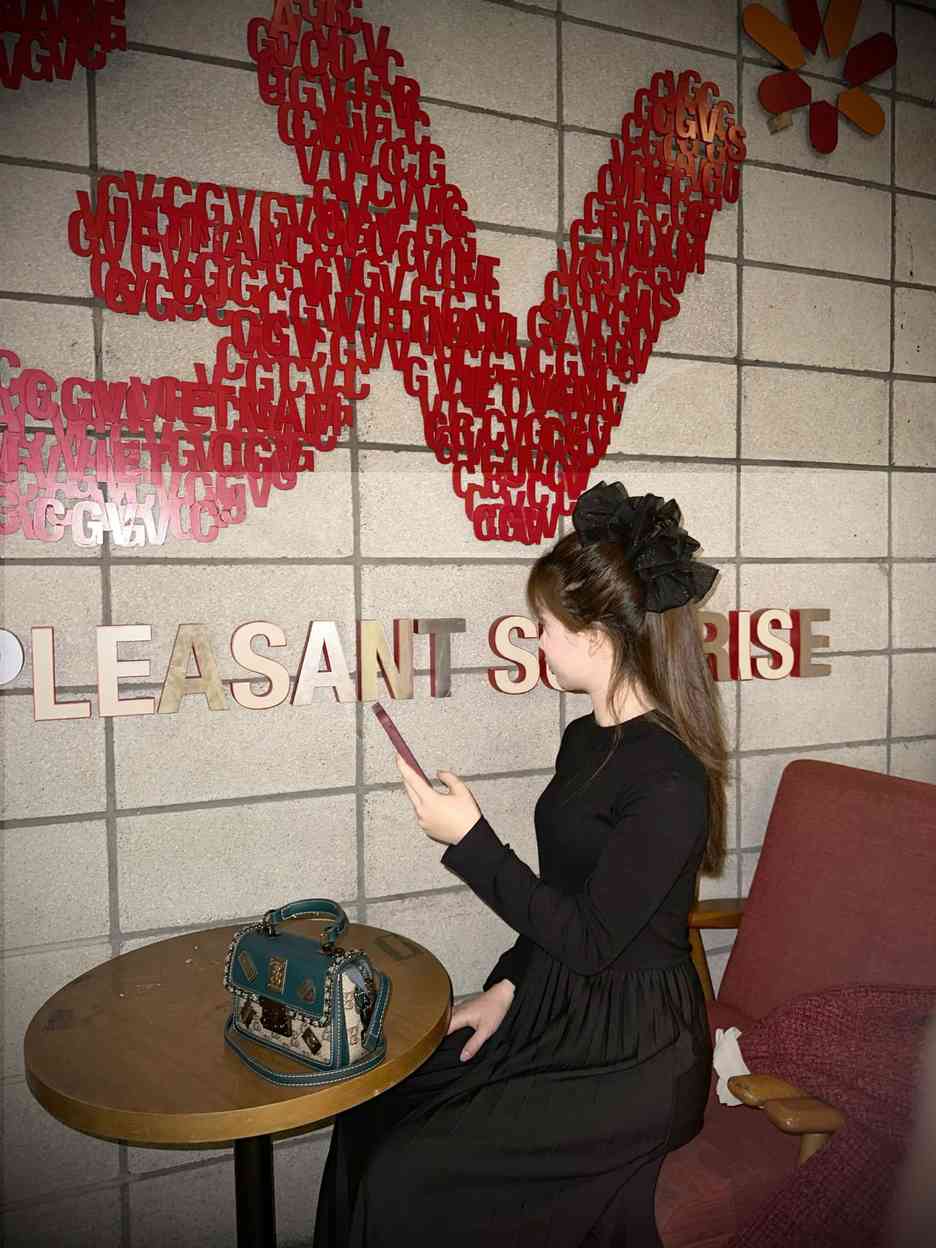Chương 1122: Đáy Uyên khiên, bên bờ đầm nước
原来如此,那这又意味着什么呢?
虽然依旧没有得到最终的答案,但宁缺距离真相又近了一步,也更接近了观主的念头。或许只是短短一小步,却已是极大的收获。
因为按照常人的思维模式,无论是他,还是余帘,抑或是大师兄,都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——或者说,没有人敢去设想这种可能。
道门想要让昊天变弱,甚至走向灭亡——这已不止是欺师灭祖那般简单,而是从根本上背弃信仰、颠覆逻辑的事,根本不可能有人会这样想!
简大家虽然也不清楚观主究竟在想什么,但她明白宁缺心中的困惑与痛苦,于是便用两段看似无理却直指本心的话语,为他指明了方向。
她用的,是轲浩然的剑,最直接、最锋利的方式。
世人常说,旅程的目的地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沿途的风景。可很多时候,那不过是失败者的自我安慰,是缺乏勇气继续前行的借口罢了。
唯有回望来路,才知那一路走过的风景,其实更加壮丽,也更加清晰。
生活如此,思考亦如此。
宁缺回望山道,望着那绝壁之间妇人离去的背影,忽然明白:若她愿意修行,必定会成为世间最巅峰的人物。只是她对那些,并不感兴趣罢了。
他由衷感激她的指点,一如感激她当年所做的一切。
从渭城来到长安之后,他一直受她照拂。初入红袖招时,她便开始管教他、提点他。只因她看着他,便想起了当年那个骑着小黑驴的少年。
想着数年前初见的情景,想着那些年在红袖招里荒唐胡闹的日子,想着简大家一言之下,令全唐国的风月行当都不敢接他的生意,想着当年腹诽的怨念与如今满心的感激,他不禁感慨良久,脸上浮现出自嘲的笑,眼中却泛起微光。
观主想要昊天变弱。
这是宁缺如今已经确定的事。至于为何如此,他心中已有模糊的猜测,却始终抓不住最关键的那道光。或许那光曾明亮过,但他不敢信。
即便太阳熄灭,生活仍要继续。
想不透观主的真正用意,无法改变人间局势,唐国与外邦的战争已然重燃。长安城中杀气弥漫,各州郡不断向边境输送粮草辎重,军部彻夜灯火通明,调兵遣将的命令一道接一道。
大唐境外也陷入混乱。叶苏的死讯令新教声势大跌,但据暗侍卫所报,并未出现大规模退教潮。想必再过一些时日,待他们舔净伤口,新教反而会爆发出更强的力量。
战争既已开启,便必须胜利——这是宁缺一贯的行事准则,也是大唐立国的根本原则。但真正要实现,却注定无比艰难。
京畿最精锐的羽林军已被调往青峡,随时准备南下清河郡。表面看,这是因宁缺坐镇长安,无需担忧城防;实则也说明,唐国正承受着巨大压力,连羽林军也不得不投入战场,随时准备野战。
宁缺站在城墙上,望着落雪,望着风雪中前行的唐军,忽然想起——“战争既已开始,就必须胜利”,这句话,似乎也曾是某个女人的信条。
叶红鱼,真的死了吗?
以观主行事之缜密、手段之狠绝,若叶苏必死,她也绝不会独活。而那夜他所感知到的,她确实已无生机。
观海僧、神殿掌教熊初墨、南海海。
面对如此阵容,宁缺自知难以逃生,更何况她?
可不知为何,他总觉得叶红鱼没有死。像她那样的女子,不该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死去。他对她,有着一种毫无道理的坚信。
西陵神殿内,死寂一片。石阶前跪满了神官执事,脸色苍白,恐惧至极。因为雷霆正在他们头顶轰鸣。
那道由万道光芒织就的光幕,在雷声中不停震颤,仿佛随时会崩塌坠落。光幕之后,那道高大的身影也在颤抖——是因为愤怒?还是因为恐惧?
叶红鱼跳入深渊,掌教与海等人认定她必死无疑,却仍不放心,派出众多高手下探深渊,搜寻她的尸首。
深渊绝壁之下,险恶万分。奉命探查的是南海一脉中一名知命境的强者,更带了无数道门高手同行。即便如此,十余日后才有人归返桃山,归来者不足五分之一。最关键的是——他们没有带回掌教最想看到的那具尸首,只能带回一个令人窒息的消息。
掌教暴怒的声音如雷霆炸响于道殿之中,阶前跪伏者无不战栗,不知自己将面临何种惩罚,无人敢言。
不知过了多久,掌教终于平静下来,声音也不再狂怒,变得低沉而阴冷。唯有最亲近的下属才能听出,那声音深处,藏着一丝不安。
“不惜一切代价,找到她,然后杀死她。”
西陵神殿虽未在深渊底寻到叶红鱼的尸身,却发现了数道车辙与人走过的痕迹。这说明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——
叶红鱼还活着。
她从栏边跃入绝壁,破云而堕,在所有人都认定她必死无疑之际,她依然活着。她做到了唯有昊天才能做到的事。
她是如何做到的?
若要从头说起,便需退回到半年前——那时,一封信离开神殿,经由最隐秘的途径,送至某人手中,悄然发出了一份邀请。
若简单些说,画面可直接切至那一夜——掌教熊初墨、中年道人与南海海围攻叶红鱼的那夜。
就在那一夜之前,褚由贤与陈七曾在道殿中慷慨陈词,代表宁缺向叶红鱼发出邀请,也向整个西陵神殿宣示了书院与唐国的轻蔑。
因叶苏之故,也因对观主心意的揣测,叶红鱼并未接受宁缺那粗暴的邀请,却也未让掌教当场将他们处死,而是将二人关入幽阁。
幽阁,是西陵神殿囚禁叛教者与魔宗余孽之地,戒备森严,无数阵法随时可杀人于无形。千百年来,除卫光明老人外,从未有人能从这地牢中逃脱。当年陈皮皮被囚于此,连宁缺也束手无策。
褚由贤与陈七被司中黑衣执事押入幽阁最深处,关进铁栅之后狭窄的囚房。那一刻,他们再无任何希望,只知等待他们的,或是死亡,或是永世不见天日——无论哪一种,皆令人绝望。
唯一令他们稍感安慰的是,自白日至夜,始终无人前来审讯,传闻中司那些惨绝人寰的刑罚,并未落在他们身上。
他们很快便想明白——之所以未被折磨得血肉模糊,未被痛楚逼至求死,只因叶红鱼。唯有她,会这样做。
她或许会在今夜或明日,冷酷地将褚由贤与陈七杀死,却不会对他们施加折磨——这已是最大的仁慈。
她拒绝了宁缺的邀请,却似乎也不愿让他彻底愤怒。
褚由贤与陈七坐在囚房中,望着石壁,沉默不语。除了一桶清水,房中别无他物,也无人送来食物。
未受酷刑,却也无人理会——漫长的等待本身,就是一种残酷的折磨。不知何时会有人进来杀死他们,这种心理上的煎熬,令褚由贤愈发不安,脸色越来越白。
陈七思虑更深。他怀疑,无人理会,是否是叶红鱼在等他们“自我了断”?安静的环境,最易令人胡思乱想。尤其是对他这样惯于阴谋之人,越想越觉得确是如此。
叶红鱼的“仁慈”,或许正是给他们一个自杀的机会。
他低声告知褚由贤,褚由贤脸色更白,犹豫片刻,低声问道:“现在怎么办?是立刻撞墙自尽,还是再等一夜?”
话音未落,囚室外骤然响起一声恐怖巨响,将他此生最鼓起勇气的话语彻底掩埋。
紧接着,一阵剧烈震动传来。深埋山腹的囚室开始摇晃,桶中清水剧烈晃荡,溅出大半。
褚由贤扶墙而立,勉强稳住身形,只觉头晕目眩。
地震了?
陈七神色骤然凝重,快步走到石窗旁,望向囚室外绝壁间的夜空。只见一轮明月悬空,别无他景。
但他听得真切——那声巨响,来自绝壁外的夜空。而震动,应源自桃山高处,说明山顶发生了大事。
不多时,峰顶又传来数声巨响,震动传入囚室,桶中清水不断溅出,湿了地面,渐渐流到褚由贤脚边。
他后退两步,望着陈七,脸色惨白:“出什么事了?”
陈七摇头:“不知。”
他们身为囚徒,自然不知此刻在桃山之巅,道门最巅峰的几名强者,正展开生死之战。
那些恐怖的撞击与震动,正是战斗的余波。
脚步声响起。二人回头,只见一名黑衣执事走到栅栏前,取出钥匙,打开铁门,目光示意他们随行。
那执事约四十岁,脸色苍白至极——并非病弱,也非恐惧所致,而是多年不见阳光的结果。
取钥匙、开门、示意犯人跟随——他做这些事时,脸上毫无表情,平静得仿佛早已演练千万遍。
褚由贤与陈七对视一眼,皆看出彼此的疑惑与不安。变故突至,却不知是福是祸。走出石室后,迎接他们的,是死亡,还是生机?
他们穿过一条漫长通道。通道由石壁围成,高约一人半,宽仅容两人并行,从幽阁后方某间库房斜斜通向桃山下,昏黄灯光将三人身影投于干燥地面,脚步声格外清晰。
无人阻拦。黑衣执事面无表情地前行,仿佛确信整座幽阁已沉睡,即便脚步再响也无妨。
通道极长。二人走了整整两个时辰,脚酸腿软,几乎抽筋,仍未见出口。陈七猛然察觉——这段通道的墙上有淡淡灰尘,似被风吹过;油灯架上的油渍还很新。
看到风痕,结合通道的倾斜与行走距离推算,他们应已接近山脚。他稍松口气——通道将尽——但随即又紧绷心神:种种细节表明,这段通道至少数十年无人通行。
西陵神殿的幽阁中,竟藏着如此隐秘的逃亡通道?是谁修建的?这黑衣执事又欲带他们去往何处?
陈七心中已猜到真相,却更加震撼。叶红鱼身为大神官,自然知晓幽阁最大的秘密,那些连掌教都不知的秘密,也唯有她,能令整座幽阁沉默。只是,她为何要暗中将自己与褚由贤放走?
通道终至尽头。黑衣执事按下一块青砖,解除机关,取出佩剑,谨慎拨开前方几株带毒刺的灌木,示意二人走出。
洞外,便是自由。
无数星光洒落夜穹,被绝壁间的云雾过滤,又被深渊底的瘴气裹挟,由乳白转为诡谲的紫色。
陈七与褚由贤望着这奇异的紫光,获释的欣喜与不解的惘然同时袭来,一时间竟怔住,不知言语。
黑衣执事却不给他们喘息之机,手掌一翻,两粒药丸已塞入他们口中。
褚由贤反应过来时,药丸早已入腹,化尽无痕。他惊怒交加,尤其胸腹间泛起灼痛与恶心,只道中毒,悲愤欲绝。
“为何不在囚室杀了我,偏要带我走这么远,走到幽阁外才下毒?给予希望后又令人绝望,这是何等折磨?难道你们神殿之人皆是变态?更何况,走这么远,我的脚都磨破了啊!”
他恐惧瘫倒,神智不清,迷糊中还在愤愤不平,无助等待死亡降临。可等了许久,非但未昏死,反而越发清醒……
怎么回事?他茫然站起,晃了晃头,良久才彻底清醒。待见星光下弥漫的瘴气,想起在长安时看过的密报,才明白——那药丸不是毒,而是解瘴毒之药。顿时尴尬至极。
他擦去冷汗,拍掉身上腐叶,走向前方的黑衣执事与陈七,正欲继续前行,却发现二人毫无动静。
深渊底部多为藤木,树冠稀疏,按理视野开阔,但实则不然。夜空星光大半被绝壁云雾遮蔽,故呈诡异紫色。站了片刻后,四周雾瘴愈浓,环境愈发昏暗。
褚由贤低头,见脚下厚积腐叶,环顾四周如鬼影般的藤树,忽然想起幽阁后深渊的恐怖传说,身体不禁发寒。
这雾瘴不仅含天地剧毒,更混杂了无数囚徒死后残留的怨念,阴毒至极。而他此刻正置身其中。
他明白,若非服下解药,此时早已七窍流血而亡。如今虽活,仍心有余悸。尤其是当耳边隐隐传来藤林深处凄厉的兽吼时,额上冷汗再次涌出。
有毒瘴,有能在毒瘴中生存千百年的凶兽,据说无人能走出这片深渊。他们,真能活着离开吗?若走不出,岂非仍是死路一条?
褚由贤心颤胆寒,不解地看着原地不动的陈七与黑衣执事。
风从绝壁吹下,林间雾瘴略散,星光重新洒落。褚由贤这才注意到,不远处有一水潭,潭对岸隐隐有黑影——看形状,竟是马车。
在这与世隔绝的险地,竟有车队?
这些马车是谁的?车上载着何人?他们在等谁?等我们?那我们为何不过去?
褚由贤今夜死里逃生,又入绝地,精神反复冲击,早已有些恍惚,脑中乱七八糟地想着。
陈七身为鱼龙帮智囊,素以冷酷著称,相对冷静。他只扫了那马车几眼,便如黑衣执事一般,抬头望向夜空。
那片夜空里,将有东西落下。
此时,他心中已隐隐明悟——书院之计,果然成功。叶红鱼,果然叛出道门。但她为何选择深夜离开?为何走如此险道?
最令他不解的是——难道叶红鱼真会如黑衣执事目光所指,稍后从桃山之巅跳下,穿云破雾,直坠此地?
桃山之巅距地如接苍穹,绝壁之间遍布凶险,深渊底瘴气滔天——任何人跳下,皆必死无疑。
桑桑能活,因她是昊天;宁缺能活,因桑桑抱着他一同坠落,在落地刹那将他紧紧护在怀中。
叶红鱼无人可抱,桑桑早已回归神国——她,如何能活?
她不能活。陈七绝望地想。掌教熊初墨、中年道人、南海海,皆如此想,就连观主,也如此以为。
桃山后麓绝壁之上,布有两道触目惊心的大阵,云雾中更藏有远古禁制。这些是道门千年积累的智慧结晶,不在神殿管辖之内,如同有生命般自行运转,借天地之力日益增强。
除却峰顶与深渊的落差,这条坠落之路最危险之处,并非瘴毒,而是代表着道门智慧的阵法。即便颜瑟大师复生,也难以短时破除,更何况在坠落的刹那,谁能抵挡?
然而——绝壁间,竟真的响起破空之声!
有人,真的从峰顶跳了下来!
陈七脸色骤然紧绷。他非宁缺,对叶红鱼没有那般盲目的信念。他总觉得,下一刻便将目睹她的尸体从天而降。
是的,正如他所想——叶红鱼再强,哪怕突然参悟颜瑟的符道神术,也绝无可能生还。
但她——还是跳了。
她被道门巨头重创,走到栏边,不凭栏远眺,而是迎着星光,平静走向崖壁,随雪花一同,向着深渊坠落。
无论如何看,她都——必死无疑。
就在此时,一道气息在深渊底的雾瘴中骤然成形。绝壁之上,同时升起两道阵意,三道气息在紫色星光间交汇。
褚由贤与陈七不明所以,却在感知这阵意的瞬间,下意识以“味道”形容——或许,这阵意,本就带着味道?
那是生铁的气息,铁上有锈,微甜中带着苦涩,又夹杂着难以言喻的刺感;紧接着,又化为石头味——更准确说,是石上青苔的味道,湿润微腥,带着植物的青涩,奇妙的是,舌面却不觉滑腻,仿佛那些青苔,瞬间枯干。
生铁代表什么?强硬?青苔与石头又代表什么?二人震惊不安,随即感到呼吸困难。
因他们胸腹之间,仿佛被塞入无数块棱角分明的石块,硌得生疼。
这是何等阵法?他们震撼回望,望向那阵意初生之处——水潭对岸的那辆马车。
——车厢之中,究竟坐着谁?竟如此强大!
Đề xuất Voz: [Review] Kể chuyện vợ chồng trẻ